推特背后的 Notch 之道
译者序
自 Notch 出售了 Minecraft,出售了 Mojang 公司后,他在 Minecraft 方面的消息也随着 Minecraft 逐年下降的热度而减少。因此也有人跟我说,微软收购 Minecraft 的那一刻是 Minecraft 的巅峰,Notch 退出得很及时。卖掉 Minecraft 之后的 Notch 经历了怎样的一段过渡期;为何在《Minecraft: The Story of Mojang》纪录片[1]中还是在 Minecon 与粉丝见面时给人的感觉都是平易近人的他,在推特上却常常出言惊人;Notch 是否还有在做些什么游戏;以及他平时有喜欢玩什么游戏。也许你也会与我一样有一些这样的疑惑。
本文是人物访谈《The Tao of Notch - Beyond Twitter》的译文版本,原文作者 Brad Glasgow,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发布在 The Escapist 网站上。[2]本人对此进行了翻译,断断续续耗时近 5 个月,文中涉及大量需要翻查各类资料后才能理解的游戏相关或非游戏相关的内容,比如詹代法则、游戏门事件与女权主义、瑞典文化、楚门的世界、以及各种美国俚语、游戏梗等等。译者翻译能力有限,如果你在阅读期间遇到难以理解的部分,可以参考英语原文进行对照阅读。同时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与翻译或者有纠错,非常欢迎(在 GitHub 仓库中)向本译文提交你的意见,感谢。鉴于翻译随时可能有改动,为保持内容一致性,本文未经本人允许不得转载。
全文总计 35000+ 字符,15000+ 汉字,图片 20+ 张。建议阅读时间至少 30 分钟。
正文
公众最近已较少听到著名游戏 Minecraft 的创造者“马库斯·佩尔松”相关的消息。在出售了 Mojang 与购买 7000 万美元贝弗利山庄巨型豪宅之后,他曾接受过一些采访,但自那以后他一直都很沉默…… 除了在推特上。
推特上的马库斯·佩尔松一直是多个论战的中心,不仅引起过一大批与他意见不一的人的愤怒,也造成过在游戏媒体中出现过多篇因为他的观点而抨击他的社论。每当他在推特上发表一个观点,一个新的社论似乎就诞生了。这些愤怒被整整齐齐地装进了网络文化大战的弹药当中。

但在所有的这些社论之中,任何的澄清,甚至一次与马库斯·佩尔松本人对话的尝试,你都很少能看到。而这就是为什么我清楚我得去采访他。如果说每次当他发布一个 140 字的重磅炸弹,一页又一页的网页就会产生的话,我想有个机会能与在这些争议推文背后那位真实的马库斯·佩尔松,来一次谈话,只为了解其中的背景。
说服他接受我的采访并不容易。马库斯·佩尔松的观点引起过大量的社论,他对记者如人所料地持着谨慎与怀疑的态度。然而,在我们开始交谈后,我发现他很友善、坦率,甚至有些潇洒。他会很认真地听,很爽快地笑。我们在 Skype 上聊了将近 90 分钟,在结束时,我感觉这不像是在采访一位自以为是的亿万富翁,而更像是一场极客之间有趣迷人的谈话。
这次采访使我想起了良好谈话的价值,这是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永远无法复制的。
The Escapist 游戏媒体(下称媒体):你想念 Minecraft 吗?
马库斯·佩尔松(下称佩尔松): 完全没有。在我出售公司前的一段时间,我就已经停止了在 Minecraft 上的工作,到我决定出售公司大概有半年了吧,所以当时看起来我不像是在工作的样子。我觉得我已经把火炬传给了延斯·伯根斯坦(Jens Bergensten)[3]。当我要卖掉公司的时候,我担心着我要如何进入我下一阶段的生活之类的事情。但在签完字之后,我就立即感觉到了解脱。我从来没打算过成为一名企业家,我只是想写代码,不想建立一个企业。不过我对此并没有感到不满。只在极少的时候,我会打开游戏看看,“哇哦,这些是我们创造的?”(笑)

媒体:所以你还有玩吗?
佩尔松: 很少很少。每隔一段时间当它从某个游戏列表中蹦出来时我会点开它,只是看看它现在变成啥样了。
媒体:自出售公司后,你已经坦言过关于突然富裕的经历。十年前你可能是中产阶级,而现在你是出名的有钱人了。
佩尔松: 在我父母离婚后,剩下一位当护士的单亲妈妈与她的两个孩子。那会儿有几个月,我记得至少一个月,她不能确定我们能否在整个月内都买得起食物。后面她让我知道了这事,但在这之前她会把事藏着并装作喜欢煮那糟糕的芬兰食物。“啊我们太穷了”,这不是说说而已,是已经成了一个家庭问题。
媒体:你在推特上说过感到孤独,你说很难搞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又只是想打你的钱主意的人。你说过你如何如何喜欢拉斯维加斯,因为你知道在那里的每个人都盯着你的钱。
佩尔松: 这好像是一年前的事了?
媒体:是的。
佩尔松: 在那之后我基本上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个状态了。我清楚,我真的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我感觉我以前就有过这个问题,这一直也是我一生的问题。所以我不一定需要有很多的朋友。而当你卖掉了你的公司,得到了很多钱,其实没有比继续学习、结识朋友以及探索真实世界更有趣的事了,只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我放弃了全部的东西,成了一个古怪的瑞典人,于是很容易变得不再想社交。
媒体:这似乎给你塑造了一个网络形象,人们认为你是一个孤独沮丧、无所事事的有钱人。
佩尔松: 是吧,我就是那样,那是我的文化观念。
媒体:这是你的真实写照?
佩尔松: 我的意思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独处,我感觉那样我才过得最高效与快乐,这不该当作我很孤独。比如我单独编了几个月的程,当然我会打算出去走走看看朋友。我会花一些时间进行学习与编程,比如玩玩 WebGL,然后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很多社交活动,比如聚会,来回做这些事。我喜欢聚会聚餐。我正在尝试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学习如何欣赏红酒。我喜欢红酒,但我总是记不住它们,比如那些老法国城堡酒庄的名字。

媒体:那现在你能说出便宜的红酒与昂贵的红酒之间的区别吗?
佩尔松: 我会假装知道!如果你在做事时充满自信那你就可以做任何事,这是让你像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方法。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像已经做过一百次那样将冰块放入你的咖啡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喝红酒时只是做个样子,亦或者他们真的可以欣赏出那些细微的差别。
媒体:嗯,我最近阅读时看到说专家们不知道白酒其实是用红色食物色素染色做成的。(注:Snpoes[4] 证实了那是假的。)
佩尔松: (笑)。我往往会去拆解与过度分析许多事情。但我会试着不去做太深的拆解,我感觉经历得差不多了,那可能就差不多了。我正在开始去尝试黑麦威士忌,因为我从未有喜欢过一种威士忌。我会说出各种各样的话,比如“啊这回味有点涩”或什么的,不过我不确认我是因为我享受它而说出来的,还是实际上感受到而说出来的。
媒体:我们谈谈瑞典吧。在颂扬炫耀财富的贝弗利山庄中生活必然会有点不和谐,在瑞典可是非常注重谦虚的。
佩尔松: 是的,也就是詹代法则[5]。我觉得詹代法则已经变得更完善了,我们非常自豪在瑞典能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谈论它谈得挺多的。它绝对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位厨师来我(瑞典)的公寓里为我做饭,对我而言真的很奇怪。我不会想这样做的。但在贝弗利山庄如果你没有厨师,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显得奇怪。这就像那些关于我进行编程和进行社交的评论。

当我在瑞典时,我只想搞我的编程。当我在编程时,我不想让任何人来这里做饭,因为我需要、喜欢我的编码空间。当我在美国进行着旅游签证时,我不会做任何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必须去真正地进行度假,参加社交活动,这样对我才有好处。显然(贝弗利山庄)那所房子只是具备某种不寻常的纪念意义的房子。人们去往洛杉矶,为的是想遇见其他人,其他因相同目的前往洛杉矶的人。这有点像是探索者与想遇见探索者的人的汇聚点。
在洛杉矶做事也相对容易些。在瑞典,大多数人在整个星期内都进行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然后在周末才可能做其它事情。所以在瑞典如果你有社交的心思的话,这会让你很懊恼的,因为每天真的没什么事情做。但是在洛杉矶,像我认识的在音乐界的人,他们的时间基本上是相反的,他们在周末会很忙。
媒体:你觉得你在瑞典的时候和在贝弗利山庄的时候有不同吗?在瑞典时会寻常些?
佩尔松: 是的,早期确实这样。那个时候可能正是我在推特上抱怨变化太龃龉的时候。知道了自己的归宿,知道了谁与你站同一边,这些都很不寻常。那会儿大概是我刚刚开始过渡期吧。现在我感觉在两个地方都挺正常的,这就像我的不同方面。我很幸运,在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已经有了内向阶段和外向阶段的一个循环。经过一些调整之后,现在也就那样了。
媒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看到詹代法则里说“不要以为你很特别。”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每个美国人都会觉得我们很特别。你来美国之后,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佩尔松: 有一点。但詹代法则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在清洁工人正在过来时,我会预先做些清理;在厨师过来时,如果我知道我很高几率会在最后一刻决定要与某个人吃饭,那么我会预先提醒他们,这样最后我外出吃饭了也不至于让他们失望。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不适应之类的,而是瑞典传统中有趣的部分。算是一种有趣的小文化吧。
媒体:你觉得你推特上的争论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吗?
佩尔松: (引起)推特上大多数争论的原因在于我真的搞不懂人们是否想过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想达到相同的目标,只是有些人选择了一些显然不是很有效的方式。你想试着在推特上(与他人)进行微妙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想着开始有意识地变得直言不讳。我看过一部名为《This Is Phil Fish[6]》的纪录片,它真的帮助我内化接受了我的自我与公众眼中的我之间的区别。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不再打算开任何公司、售卖任何游戏——我意思是我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卖游戏,但这不再会是我的主要驱动力。我想通了,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管网上的人怎么说,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的朋友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才将推特作为一个强大的临时演讲台。

媒体:现在的你已经相当富裕了,在卖掉 Minecraft 之后,你有感觉到一定的自由了吗?我就不能在推特上畅所欲言,因为我会担心出版社怎么想,但似乎你拥有这些他人没有的自由。
佩尔松: 某种程度上吧。更多的是有时候我会跟一些私下找我的人交流,比如一些职业人士,他们会说“谢谢你能把这些讲出来,但我们不能(公开)支持你”。也有少部分私下联系我的人会说“嘿,虽然我还是你的朋友,但是你看起来像个白痴”。不过私下联系我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认同我的。所以我才觉得,这也许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一个机会,去表明实际上是有可能在推特上发表意见而不用作出牺牲的。
媒体:但有些人觉得你就有这个责任,他们批判你在推特上反应过度。说某个只有几百粉丝的人推上说了你一句混蛋,你给那个人回了句婊子(cunt)……
佩尔松: 要说一下,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个词原来这么刺耳!我经常在 Twitch 上看的一位澳洲朋友就经常说 cunt 这个词。感觉像是一个 cunt 抵过了八个 fuck 什么的。我会更少地用这个词吧,但是我依然坚持我说过的话。
媒体:这是你在美国能说的最糟糕的一个词了。
佩尔松: 文字本身并不是魔咒,因为沟通是围绕着你知道或相信你的听众会以相应的意思倾听你而进行的。如果你说出“cunt”这个词时已经知道这个词很无礼,那么当你说出口时你的意思就是为了冒犯他人。这就是文字给你的反馈循环,而且会愈发极化。我不常在推特上骂人。我不避讳骂人,至少我以前在现实生活中就做过挺多的,不过最好还是少点使用。“cunt”这个词确实是太强烈了。不管怎样,反应是过度了……
媒体:你在推特上拥有 380 多万粉丝,这个数字有带给你一种别人没有的责任感吗?
佩尔松: 并没有。对此我的回答是不要去得罪比你来头大的人。这是让我保持中立的方法策略之一——这里不仅指我。我感觉像“啊,你不能向我发起你的粉丝攻势,我只有 200 个粉丝,而你有 700 万”这样的指责,已经成了过去几年来的一种趋势。所以这是一个只能单向进行的对话么?其实如果只是给我一个私信,我会尽量不跟他们较劲,除非是我真的很生气亦或是被嘲讽了。但如果是公开地说我事并且已经将事情传开了,那毫无疑问我会同样公开地去回应。我感觉有时候他们是故意诱导我的,然后他们就可以抱怨我如何把我的粉丝攻势压到他们身上。
媒体:我们聊聊你推特上一些具体的争论吧。我想从“直男癌(mansplaining)”争论开始。你说这是一个带性别歧视的词。我相信有两大篇(社论)文章是因为这事而写的。
佩尔松: (笑)

媒体:你认同直男癌这一回事吗?你是否认同男性会过分解释事情或利用太多权威去解释事情?
佩尔松: 是的,而且我肯定见过这类事。我的观点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必须互相平等,要把每个人都视为个体对待。你不能随便就以“男性在谋杀案中的代表性过高”来认为每一个男性都是凶手。我们说的是谋杀(murder)而不是男性谋杀(man-killing)。自以为是(condescending)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词,然后你又搞一个直男癌出来,本质上就是性别歧视。不过对于男性来说,这个性别歧视似乎没什么大不了,难道是因为我们掌握着权力等东西?
媒体:你还提过“ovary-acting”这个词。(译注:词发音通 over-acting,即反应过度,ovary 意子宫;该词特指女性反应过度。)
佩尔松: 那个应该是其他人提的,我提过的是“cunt-fusing”。(译注:词发音通 confusing,即混淆,cunt 意婊;该词特指女性混淆事情,与直男癌有类似效果。)
媒体:噢?是吗?
佩尔松: 是的,那时我还不知道 cunt 这个词这么糟糕,这个双关语不太好。ovary-explaining 会是更好的词,我当时应该用这个的。(译注:词发音通 over-explaining,即过分解释,ovary 意子宫;该词比起 cunt-fusing 更加能与 mansplaining 有类似的声形意效果。)
媒体:Destructoid[7] 网站还因为这个写了一篇只能说是有抹黑之意的文章吧,宣称你“受到了女性的压迫”。
佩尔松: 我并没有觉得受到了女性的压迫。
媒体:(Destructoid)他们有尝试过联系你吗?
佩尔松: 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大概也没必要跟他们对话,不过我记得的确是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还有一点就是,我真的不太想那些想采访我的人联系我。
媒体:那你有读过那篇文章吗?
佩尔松: 我读了开头的部分,后面的简单扫了一遍。我通常不会看关于我的文章,即使是说好的方面的,因为看这些会让我不停地自我怀疑。我觉得在阅读时得克制住自己,这样才能看出他们在用什么奇怪的角度来评论,然后我才能予以回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也算是一种自我释怀吧。我明白发生了这种事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
媒体:没有改变是指什么方面?
佩尔松: 我实际的日常生活。我依旧可以和我的朋友玩玩棋类游戏,可以不去上网就只玩棋类游戏。在这些事发生之前,我会想“上帝保佑,希望不要出现诋毁之事”什么的。而在发生后,我觉得“哦,还好吧”。而且在推特上关注我的大多数人似乎是站我这边的。
媒体:我们谈谈关于审查的争论吧。你谈过关于自我审查的事。在 Reddit 上你参与过关于有玩家希望任天堂将林克设定改为女性的讨论。那些要求林克设定为女性的玩家是何以(自我)审查的?

佩尔松: 你的用词表达是正确的。你刚刚说“要求”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对他们为自己的艺术表现作出牺牲的要求。(这事)教知人们社会上正在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即使他们(游戏角色)不是真实的,但如果你认真了,那就很重要。很久以前我就没再用“他(he)”来指代一个未知人物,我会说“他们(they)”。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清楚他们想要那样做(要求林克为女性)的原因。然而对于我而言,《塞尔达传说》并不是一个关于性别的游戏,所以翻转性别对我一个玩家来说真的没什么意义。我明白他们为什么想要这么个象征形象,但是要求别人代表你这样做就显得有些奇怪。我觉得将塞尔达和林克的身份对调会更加有意思,有一个女主角和一个被困在魔王加农的城堡里的男性角色之类的。身份的翻转使得在游戏里会有一些新的事物发生,这会变得非常有趣。
媒体:所以总的来说如果玩家要求更多女主角,你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吧?
佩尔松: 嗯,如果是关于这事的良好谈话或者是一些公论都是挺好的。只是问题在于这整个讨论就像被感染了一样,像《守望先锋》猎空的那事[8],其实原来的帖子并不像是要求些什么,并没有要求进行调整,只是说那个姿势对于猎空这个俏皮女生角色太过性感显得有些奇怪,开发商认同了这个不适而已。可是有玩家不想开发商调整猎空性感的姿势,然后舆论就爆炸了。实际上原帖说的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被(怨气)感染了,导致很难有任何良好的交谈。他们把猎空的姿势换成了一个真正的 pin-up 姿势,我觉得这做的非常正确。他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不是想让猎空显得性感,而是想更符合她的活泼感。他们赞同了原来的姿势显得标准与一般,并把它改成了一个调皮的 pin-up 姿势。他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令人印象深刻。

媒体:你在推特上谈过多元交织女权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9]。你说那是一个“偏见的体系”,可以说一下原因吗?
佩尔松: 有些人因为他们的身体特征而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特权,继而认为每个拥有这些特征的人都比那些没有这些特征的人更具特权性的话,这样的观点就是最直接的偏见。并不是每个白人男性都会比黑人女性能赚更多的钱,虽然作为一个群体平均下来的话确实这样。但这样很容易脱离概念以及忽视社会趋势,变成真正的“直男癌”。我认同直男癌是有出现的,但你却因为我有观点想要说,就利用直男癌这个说事堵住我的嘴,即使我没有摆架子。然后你又提出这么一套为一些大相径庭的东西而建立的体系,这会很容易错用来攻击个体,而非群体。
媒体:多元交织女权主义者阿妮塔·萨琪西恩(Anita Sarkeesian)在你家参加一个派对时拍了一张照片,你因此受到了一些批判,一些人说你“不要屈服于女权主义!”。你有看过她的《游戏情节与女性(Tropes vs. Women in Video Games)[10]》系列视频吗?

佩尔松: 我看了某一集的一部分。对我而言,我对游戏与媒体产生的文化影响并不感兴趣,我更喜欢(研究游戏)物理。我知道这是一场很不错的讨论,正如我说过的,这也是在谈论这类事情时我不用“他”来指代一个未知的人物的原因。我自己看了某一集的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真的与我不大相干。我并没有直接邀请她(参加派对),是我的一个朋友带她来的。我跟她见了个面并交流了大概 30 秒,她很客气,我也很客气。我们从未谈过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事实(可能吧,因为我没看过她的视频)。对我来说就像是与普通人见面一样。你也不会跟你的父母讨论政治问题是吧,人归人,她人很好。人们喜欢说“喂,她没有被邀请,她是偷偷进来的!”。想一下,有哪个朋友的朋友真的收过邀请呢。
媒体:我们谈谈社会正义战士吧。(译注:SJW,全称 Social Justice Warrior[11],亦即键盘侠)
佩尔松: (笑)
媒体:不好意思,我不是想在这里找你麻烦的!
佩尔松: 没事,还好啦。
媒体:一部分人觉得“键盘侠”这个词只是特指某一个人。他们认为键盘侠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想伸张社会正义的好人。你觉得你是一个键盘侠吗?

佩尔松: 是的。当然我觉得这话有点稻草人谬误[12]。比起说某个个体是或不是键盘侠,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更广泛的运动。每个人都可以转变成键盘侠,可能取决于一天中的时间、你的心情、跟你闲逛的是谁,或者是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对我而言,我会用键盘侠这个词,因为它可以惹怒别人,它更多代表的是那些人的烦躁与愤怒。就像建立这种文化本身一样,我们得担心我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得罪别人,有时候会担心到一个非常荒谬的程度。我在 Reddit 上看过说键盘侠会宁愿把楼梯给去掉也不愿意在旁边加装一个舷梯,因为他们觉得在楼梯旁边加装舷梯会显得很唐突。记得我在推特上发过这个,我觉得这样不太实际吧。我认同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至少有相同的机会。如果你最终成了一个混蛋,那你就该被对待混蛋一样对待。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样的机会,我们应该尝试去包容,但也不能只是一昧地去迎合大众。我们不能在彼此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交谈。也是因为这个越发苛刻的环境,导致有一帮喜剧演员不喜欢到大学校园中开演。所以说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像自我审查般的文化运动。
媒体:有很多人在推特上公开抨击你,他们很令人讨厌。
佩尔松: 是诶。
媒体:这些人,就是我们正在说的,典型的键盘侠吗?
佩尔松: 不不,这完全是随机的。我认为原因在于“社会正义战士 vs. 游戏门提倡者”变成了一个非常势均力敌的问题。如果你有看过 CGP Grey 的《This Video Will Make You Angry[13]》视频的话,就明白这一观点的对抗深挖下去其实就是源于一个观点和立场罢。键盘侠与游戏门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所以搞得每一个单独的问题都会很奇怪地以某种方式与其联系上。有时候我会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发一个推文表达我喜欢某种类型的音乐,比如说挪威并不存在真正的音乐形式或者爵士并不是真正的音乐形式云云,然后就会影响了一些人过来抨击你。很多情况下这只是开玩笑,虽然有时不是。我倾向于认为人是本善的,而且我清楚,在我还年轻和无名时我就一直是这样,只是想表达一下意思。这就像枕头大战一样,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想要去伤害别人,更多的只是想去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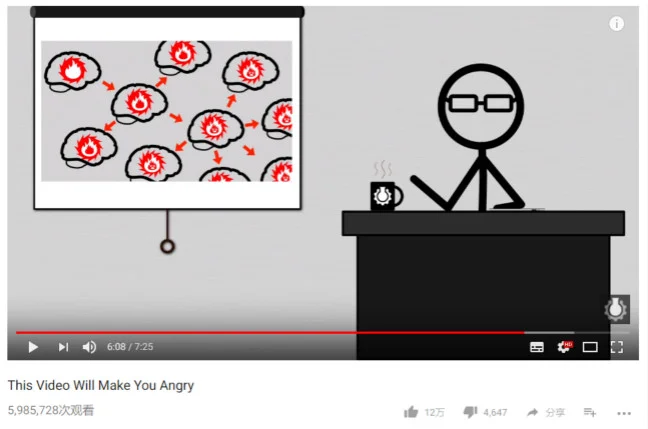
媒体:推特上的一些人指出你有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c)[14],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佩尔松: 哈哈,这只是一个容易给人贴标签的词吧,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媒体:我看了你的推特和采访,并不清楚这个断言是哪来的,但就像我说的,它就是摆在那儿。如果你去搜索的话,会看到有人说你是垃圾、反跨性别者。
佩尔松: (笑)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出现的。可能是因为我在某件事的某个点上拒绝了做出选择,又或者是因为我对此做出了什么反应,于是就被扣上帽子了,不清楚。我真的不在乎人们怎么做,我没有跨性别恐惧症。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去表达自己,同时不必在乎别人怎么做。我不是鼓励人去改变自己的性别,如果有人说要去变性,那么祝安好!如果你对此有话想说,我洗耳恭听。至于其它,我不在乎。
媒体:如果一个男人转性成了女人,那个人现在是女人吗?你会用什么代词称呼?
佩尔松: 看他们想被怎么称呼。我觉得很荒谬的是,你的身体属性必须要限制你如何表达自己,尤其是在网络上。我的意思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是以特定方式出生的,我们不应该忽略现实存在的事实。但性别标签更多的是表意说法,尤其是在网络上。所以即使某个人并没有转性,但是希望被称呼他或者她,又何妨呢?为什么会有人在乎这个?我才不在乎你有一个蓝色的头像呢。(译注:蓝色的头像指网站默认的男性头像)
媒体:好吧,我们继续谈下游戏新闻业的话题。你明确表明过无论如何你绝对不会是游戏新闻业的粉丝。你称 Kotaku[15] 是“键盘侠的传声筒,试图死守道德虚伪与权力炫耀的沉船”。
佩尔松: (笑)

媒体:电子游戏新闻有什么问题吗?你不喜欢它的什么?
佩尔松: 我喜欢,也会去读。但它只是一种流行文化,并不是新闻业。然而他们总喜欢说“对,但我是一名记者!”,好像他们在生活中有一些明显的特权一样。但这不是新闻业,他们并不是记者。他们会说“可是我们不应该去谴责一个没有女性林克角色的游戏吗?”,对此我只能说“不”,因为这明显与新闻业核心基本原则相悖。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名新闻记者,就应该尽可能做到客观,将其视为主要特征之一。但玩家并不喜欢阅读那些冰冷的、事实性的游戏新闻报道,所以就使得这更像是……怎么说呢,所有这些报道都成了主观的文章或社论。他们自称为新闻记者,却在讨论虚拟现实里的乳摇如何奇怪,讨论如何浪费 20 分钟重新载入游戏,又或者讨论他们小时候的奇闻轶事,以及讨论枪支利弊。我是瑞典人我不喜欢枪支,但在一个关于虚拟现实的视频里谈论枪支的利弊,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媒体:你刚刚谈到了新闻业的一般性与客观性。但也有一些记者和游戏记者说客观是不可能的,最好是坦言偏见。对此你有何想法?
佩尔松: 我感觉对于娱乐而言一定会有客观的余地的。一定有客观的余地,只是那些游戏记者不愿意去尝试客观。读懂那些与你意见一致的人也好,看清那些与你意见不一致的人也罢,阅读(本身)是挺有趣的。要是声称客观性是不可能的话,那科学性呢?我们——我这辈子没搞过科学,不能说“我们”(笑)——科学家们就摆脱了整个观念尝试去使得所有事情变得可度量。当然,搞硬科学比起像心理学这些更模糊的学科要更容易些,但对没错,人会抱有偏见这个还是得承认的。不过我们不应该仅仅接受这个事实,而应该尝试去编制一些工具来克服偏见。否则就会变成像《This Video Will Make You Angry》视频里说的那样,为了大声表达观点却在相互大嚷大叫。

媒体:你提过游戏门[16]的事,对此你是有何看法的?
佩尔松: 这事发生后,我不敢相信,觉得为所有涉事的人感到羞愧。(这其中)很多人做了很多错事,但我觉得还没夸张到造成这狗屎局面的程度。关于 IGF 的评委存有偏见等的谈论,就像是一场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小型竞赛。那些参评的人本身就来自社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喜好这是必然的。这甚至一点都不用意外。这就好比奥斯卡,如果说某人拍了一部关于一匹马的电影,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奥斯卡奖。你可以看得出可能是因为属于他的时刻到了,(获奖)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最佳的实际表现,在幕后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未实际看过《荒野猎人》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看得出那是属于它的时刻。这并不是宣称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只是因为要庆祝它。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没错,因为你喜欢你的朋友,所以你可能会偏袒他们。你偏袒他们,是因为你真的清楚他们创作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其中那些相当细微的事情。
媒体:一些游戏新闻记者已经在推特上公开抨击你了,比如 Rock Paper Shotgun[17] 的人说你是“混蛋”。
佩尔松: (笑)他们说的没错!

媒体:现在他们对你的态度与三年前有不同吗?
佩尔松: 额…… 是吧?只是我觉得三年后今天的环境也已经改变了。
媒体:怎么改变?
佩尔松: 我觉得在那时他们实际上赚到了钱。如今所有游戏门相关的东西你都得去站边这事变得越发重要了,否则其他人就会问你“你支持哪一方?!”。只有很少人能够避而不谈,在这方面 The Escapist 做得很不错。你必须得站边,自然也就同时选择了你在“游戏新闻业”——这里有个很大的双引号,中的其他朋友。因为你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的,这是你的文化。而不是些什么邪恶的阴谋。
媒体:所以你认为游戏新闻业在这场文化大战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吗?
佩尔松: 不,并不是全部吧。像 Rock Paper Shotgun 我以前挺喜欢的,现在……呃。还有 Polygon,感觉是不是他们已经不喜欢游戏了?
媒体:我见你说过一下那个关于 Polygon 游玩 DOOM 的视频的事[18]。

佩尔松: (笑)事实上,对于那个视频他们不是用“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太高兴,好吧这太搞笑了”之类的解释拥抱玩家,却用“不,我们只是写游戏文章的人,不是游戏专家!”这么个荒诞的借口。我想说,体育评论员是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但是如果你是评论足球的,你就得知道怎么踢足球。如果你是评测游戏的,当然你就得懂怎么玩游戏。
媒体:你已经说过很多次在业内有许多人不能公开地支持你,只在私下对你表示支持。其原因在何?
佩尔松: 因为他们不想卷入其中,不想惹来关注。也许是他们觉得我所做的对他们来说不太重要,他们不想他们的声誉被玷污,不愿意 VICE 上有写抹黑他们的文章。而我也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抹黑诋毁的文章,原因是他们(媒体)想确保(公开支持)这种行为会收到惩罚。然而幸运的是,我并不在乎。
媒体:这就是我们刚刚谈过的自由吧。
佩尔松: 我也认识到事实上这只是我的事情。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想待在家里了解(游戏)物理如何工作。
媒体:这些人没有走上台支持你,你有觉得难过吗?
佩尔松: 不,并没有。其原因我完全能理解,这也没什么。人们只是在网络上有政治观点而已,又不是真的快要饿死的情况。
媒体:推特上的论战有令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失去过什么吗?

佩尔松: 我感觉有一部分人挺荒诞的,他们声称支持我但其实并不是,然后却反过来想我去支持他们。之前唯一一次我跟其他人说过这事是跟 Danny Baranowsky[19],他为《节奏地牢(Crypt of the Necrodancer)[20]》创作了非常棒的游戏音乐。我很喜欢他,虽然他并不认同我。我们在今年三藩市的 GDC[21] 上碰了面,他对我说了声“嘿,恭喜啊!”的话,因为我拿了个奖,是大使奖还是什么来着——啊我应该记住我拿了什么奖的(笑)(注:其实是先驱奖)。他知道我们在不同事情上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祝贺了我。我知道他不认同我,但很高兴他祝贺我了,我尊重他。
媒体:你在游戏行业的人脉呢?他们通常是怎样的么?对于你在推特上的论战他们能应付得来吗?
佩尔松: 也许吧。
媒体:他们中有人给你发过私信告诉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该说吗?
佩尔松: 早些时候在我谈论一些事时有人联系我,最近没那么多了。我忘了那时我说了什么,他们联系了我跟我说“不,这个问题事实上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接近那些人。感谢他们告诉我吧,虚心学习。我遇上太多屁事了,人们给我发威胁邮件什么的。这些似乎在女性那边更加糟糕。
媒体:关于推特的论战就谈到这吧。在出售 Minecraft 之后,你在告别信中说“如果我偶然间再做了一些看起来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会马上放弃它”。现在的你还是这样想的吗?
佩尔松: 现在不一定了。我是害怕再对一款游戏担负起责任,因为一旦这样你会被诱使一直做下去,粉丝们的即时反馈是有点令人上瘾的,你会不想让粉丝们失望。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也难免让我觉得我好像无意地陷进了一段感情中,如果让所有人失望了,压力会很大。

媒体:你说过这也是你出售 Minecraft 的原因之一。是粉丝们的意见与要求给你带来了负担?
佩尔松: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还是会想做出我能做的最好的游戏,亨利·福特不是说过一句话嘛,“每当我问顾客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需要跑得更快的马”[22]。
媒体:嗯嗯。(注:看来历史上一直误认为是福特说过这句话。)
佩尔松: 我感觉这情况对很多游戏开发者来说还挺常见的,不过不是以这么一个束缚的方式出现。没错你得去倾听玩家说他们想要什么,但是你才是做游戏的人。你了解游戏,可能玩过很多游戏,知道怎么去创新,更加清楚怎么发展它。所以不是说玩家要求游戏怎么怎么样,而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去提炼出玩家真正想要什么,或者是他们对哪部分存有疑惑。我是想做出我能做的最好的游戏的,因为乐趣就在于做出一款伟大的游戏呀。
媒体:我看过在推特上有个人跟你有一个对话,说你是第一个发布 Alpha 版游戏的人,掀起了一股趋势:人们开始发布一些未完成的、充满 BUG 的烂游戏。那个人说你对此有责任。Minecraft 似乎是第一个如此成功的游戏,你觉得你有责任吗?
佩尔松: 不,我这么做是因为看到《表层指挥(Cortex Command)[23]》是这么做的,并且他们也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我思考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独立游戏开发者破产倒闭。我开始也想过我将会怎么做,该如何做游戏,因为我从来没拿过一款(未完成的)游戏实际去收费。我希望能出售的是一个成品,能以之为荣。而在我见识到《表层指挥》如何获得社区的参与支持之后,我就想如果我早一点开始收费也许能成吧。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如果我没有早点开始收费,我觉得我会完成不了 Minecraft。现在开发者们能有这么一条出路,我觉得是很好的。如果有吸引人的地方,人们还是会买单的,尽管有过一些失败的例子。我所知道最好的例子就是 FTL 了,《超越光速(Faster Than Light)[24]》。

媒体:我见你说过这个游戏很多次了。
佩尔松: 它是一款相当可爱的小棋盘游戏……
媒体:这游戏伤我太深了!
佩尔松: 哈哈,在 Twitch 上你会看到有人在玩无暂停的困难模式。这游戏的氛围和音乐做得真的是淋漓尽致,对发行商来说这些是很难(做到)的。
媒体:FTL 里面所有的飞船你都解锁了吗?

佩尔松: 没呢。最早我是在 PC 上玩的,之后是用 iPad 玩的,感觉更赞。后来由于我的 iPad 丢了就换了一台 iPad,大概解锁了 4 个飞船吧。最近我没怎么玩了,现在买了新的 iPad 又得重新来过。
媒体:好吧。接下来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目前正在做什么吗?
佩尔松: 我正在做一些东西,但这个会尽量不让任何人知道。
媒体:是新游戏?
佩尔松: 哈哈,做游戏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了。玩家抱怨我用 Java 写的 Minecraft,这个新东西是用 JavaScript 写的,我在努力。(笑)
媒体:这一定很有趣。
佩尔松: 是一个关于要找到最长可能路径的荒谬性的东西。很有趣!
媒体:前面我们谈到过关于你在出售公司之后对于后续生活的理解。这个你已经想透了吗?还是说正在这个过程中?
佩尔松: 还没,不过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不用再去想通这事了。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时,你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东西。人们往往享受扮演惯常的角色,因为已经习惯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过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就挺好的,这只是 1% 的人会埋怨的事情。但你必须运用不同的技能来驱动你自己,这样你才不会一个星期穿着内衣坐着只是在打代码,令一切变得糟糕。你不能依靠闹钟响来驱使你早上去上班,需要去学习各种新的技能。去习惯不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媒体:许多人好像非常关心你正在做什么事,是否还有生活目标。福布斯杂志有一篇文章说你“已经到头了”,认为你没有目标,没有项目。你觉得你需要定一个目标或项目吗?还是说你接受了这番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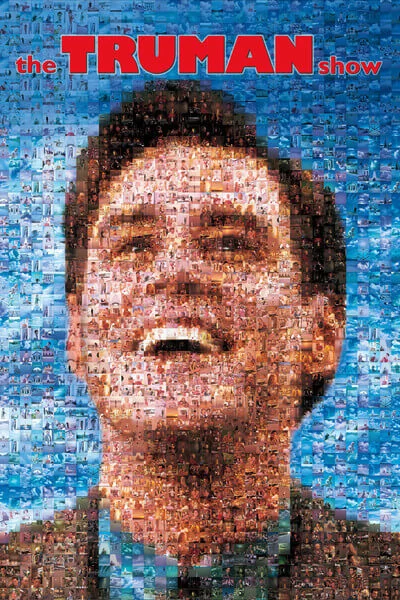
佩尔松: 我感觉这有点像《楚门的世界[25]》里面的结尾,当楚门最后穿过拍摄场地时,所有的事情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我是虚无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觉得“真实”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词,因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个主观现实,我们是这个主观现实的组成部分。显然,所有事物都是这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其它任何数学概率显得要真实。我不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目的性的。大概还可以说我是无神论者吧?我在尝试坚持“尽可能创造出更好的故事”的生活模式,因为当我离开人世后,剩下的只会是那些发生过的为人所知的事情。所以如果我有试图去创造一个有趣的故事的话,那我认为我已经尽力了。我不觉得有什么是我要做的。当没有了日常生活的框架去认知你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变成去放纵看完《绝命毒师》,而不是去做一些能创造更好故事的事情。所以,我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并不清楚。但我已经成功放弃了一家公司和它的员工,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想过得到那些。只是因为 Minecraft 变得庞大了,我才必须去做这些事。至于编程?我一直都有在做。
媒体:好吧,接下来我们进入限时抢答环节吧!
佩尔松: 喔不。

媒体:你有吃过鲱鱼罐头吗?
佩尔松: 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吃过,鲱鱼罐头本应是挺恶心的,我不记得那时我是真讨厌它还是假装讨厌它了。在我们出售公司之后,雅各布(Jakob Porser[26])还想让我再吃一次。我的反应是觉得他很无聊,因为我已经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吃了。
媒体:挪威有多糟糕吗?
佩尔松: (笑)前些年是我们分离成两个国家的 100 周年纪念,文档里说我们进行了一百年的暂时分离,之后会重新谈判。其实并没有人关心这个,那时人们只是觉得“无所谓啊,你的国家是你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提这事呢”。我在想“他们有很多石油啊”。其实我真的挺喜欢挪威的。
媒体:这真是一场伟大的对抗。
佩尔松: 我认为这跟詹代法则有点联系。其实不管是瑞典人抱怨挪威还是反过来挪威人抱怨瑞典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有人去说挪威的话我会觉得不高兴。
媒体:一个富有的人会知道贫穷是什么样的。如今当看着物品的价格时你还会带着贫穷的心态吗?仍会觉得“什么那份牛排要 200 美金!”?
佩尔松: 会的会的。这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买不起,而是感觉像是被骗了。如果真的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推销员向我推销牛排的话,我可能会尝尝:“好啊,来跟我说说这牛排到底有多好”。如果不是美味势不可挡的话我想我不会再去吃了。我比想象中要更关注商品的实际价格。我会将“我知道一条面包的价格吗?”作为现实检验的方法之一,结果就是我会跟踪一些价格动向。
媒体:你会烹饪吗?
佩尔松: 不会。主要是我觉得烹饪很无聊,做饭比吃饭要花更多时间。对于烹饪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想象。就类似于室内装饰,你问我“你想要什么样的椅子呢?”,我会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有什么样的椅子吗?”。烹饪就跟这个一样,你问我“你在做什么食物吗?”,我会说“我不知道呀。”,然后做了一个很不错的卡布纳拉意面。

媒体:那瑞典肉丸呢?
佩尔松: 我可以买冷冻的,然后把它们放进锅里煮到不再冷。很美味!
媒体:你喜欢电子音乐,这是众所周知的。你有不喜欢的音乐流派吗?有哪些音乐是你不能忍受的?
佩尔松: 唔……
媒体:乡村音乐?
佩尔松: 这可能是离我最遥远的音乐之一了,还有我开过玩笑的爵士。不过我并没觉得这些流派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从来就没有对它们大加赞赏。如果我喝醉了我可能会欣赏任何类型的音乐,酒精最大的一个作用是能让音乐变得美妙。记得我在克里夫兰的一家酒吧里和一群拉着小提琴、吹着口琴等搞演唱会的人在一起庆祝圣帕特里克节,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们中夹着奇妙的音乐,很棒的氛围。
媒体:你接触过许多大明星,其中有让你特别追崇的吗?
佩尔松: 最强烈的大概是约翰·卡马克[27]了。
媒体:那可真是极客啊!
佩尔松: (笑)小时候我有几年梦想在做 DOOM 引擎(好长的一个梦!)。不过不是梦想发明了它,而只是想去理解它并把它重建出来。这件事成为了我的依托。在只查看文件格式没有看源代码的情况下,我想我已经从头写过两次这个引擎了。遇到约翰确实很是深刻。
媒体:是时候找下你麻烦啦。PC 和主机你更喜欢哪个?
佩尔松: 我会选择 PC。我觉得如果你有几个好基友、几份爆米花和啤酒的话,那么你可能会选择主机。记得我曾喝醉了在(主机上)玩《基友大合体(Mount Your Friends)[28]》,非常有意思,但这在 PC 上则很难操作。对于我来说,我会更喜欢呆在房间里,坐在一台电脑前面,对着我的耳麦说话。
媒体:你有玩过多人游戏吗?比如《火箭联盟(Rocket League)》?
佩尔松: 我试玩过《火箭联盟》……
媒体:现在所有人都去玩《守望先锋》了。
佩尔松: 是的,我之前还玩《军团要塞 2》,现在在玩“军团要塞 3”了(注:佩尔松以此称《守望先锋》)。
媒体:你在《军团要塞 2》里用什么兵种?
佩尔松: 主要用的是士兵(火箭兵)。Valve 为我的所有角色做了一个立方体像硬纸板箱子一样的自定义帽子(头套)。所以其他玩家能认出我。我还获得了 2~3 个口袋间谍和口袋医生(饰品),有点感觉我跟其他玩家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我太相信人了,不会做检查间谍(Spy check)。我喜欢发射火箭,擅长发射火箭来背刺别人。

媒体:你会玩火箭跳吗?
佩尔松: 哈哈,肯定呀。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守望先锋》里面法拉的设计,因为她跟火箭兵相似,像是一个飞行着的高贵的骚扰者。在游戏中我会试图保持高度优势,这很有趣。但是她的大招是定在地上发射非常不准的火箭。我觉得如果她的大招能多一点移动性的话会更加有趣。像我会建议大招是一个地面猛击,从越高的地方冲下来,落地时的攻击力和击退就越高。相当于用高度换取了击退与攻击力,然后(后摇)卡在地面一会。做成像是——“现在,我要下来了”,然后使用大招,或者是在更高的地方使用——“我要把他们都撞倒!”。这样比定在地上射击,会更加符合这个角色吧。
媒体:有哪个你最喜欢的游戏是现在正在玩的?
佩尔松: 我已经有点厌倦《守望先锋》了,目前在重玩《GTA V》。他们做了个迷幻仙人掌的彩蛋,吃下后会变成大脚怪。在 Reddit 上还有玩家在讨论关于千年山秘密的事,试图去揭秘这些阴谋论。(知道这些后)我感觉“卧槽,这游戏藏得很深呐”。

媒体:你对车感兴趣吗?
佩尔松: 我以为在我有钱之后我会买一辆豪车,于是在一年半前我去考了驾照。然而在我拿到驾照后,我只开了大概最多八个小时。我认识到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开车。
媒体:于是你可以在《GTA V》里面开车。
佩尔松: 是的,在《GTA V》里没有限制只能右转弯,你不必忍受交通堵塞。而在斯德哥尔摩,所有街道都是单向的。在《GTA V》里你可以在马路中央的分隔线起动,这很荒谬但也很有趣。
媒体:在《GTA V》里你有帮会吗?以及有玩过抢劫模式吗?
佩尔松: 没有。我第一次玩《GTA V》时还没有抢劫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帮会,里面大部分是 Mojang 的成员。后面玩抢劫模式两三次后发现要更多的队友,然后每一次玩的时候匹配到的人好像都是 Polygon 的员工(译注:嘲讽匹配到的都是不会玩的)。
媒体:你觉得虚拟现实是未来趋势还是昙花一现?
佩尔松: 必然是未来的趋势。我在生活中初次使用时(就觉得它)已经足够实际应用了。

媒体:HTC Vive 和 Oculus,所有这类设备你都用过吗?
佩尔松: 我之前用的是 Oculus Rift DK2。我知道他们说打算给众筹者们送出正式版的产品,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也不会介意的(笑)。因为 Facebook (收购的事)真特么吓到我了,以及我也不想虚拟现实被……
媒体:用来挖掘你的数据?
佩尔松: 是的,我不想它监控我的电脑并把信息发给 Facebook,这个我想想都害怕。而 HTC 做事对比之就好得多。Vive 是有点重,带在头上挺沉的,但它有几乎和头显一样大的控制器。玩家拿着控制器就会感觉很直观,不会觉得只是有多个显示面。非常棒。
媒体:你有想过做 VR 的开发吗?
佩尔松: 有的,我之前在第一版的 Oculus 上用 Unity 做过一些实验,了解为什么玩家会产生作呕等等的问题。之后我打算等它更好的版本出来,从 DK1 到 DK2 的进步很惊人。后来我想过去继续这个项目,但我却转去玩 WebVR 了,这东西虽然有点天马行空,但胜在能用,它的 API 非常简单。
媒体:你的 PC 呢?是你自己组装的吗?
佩尔松: 没,大概 10~15 年前我就没那么做了。以前我很热衷于这个,每隔几年出来的 CPU 等产品我都会很清楚。直到后来我发现比起硬件我对软件的兴趣更高。现在我不再了解我的 PC 里具体有什么了,因为我有朋友会推荐这么一套 PC 架构,并且做一些个性化来适应你的需求。我会跟他说“整得很高大上我才能向人们装逼啊”云云,不过他基本上会认为你只是在为了烧钱而烧钱,并且会帮你进行缩减。于是我有了一台很棒的个人电脑,让我挺高兴的。
媒体:你是某些物品的收藏家吗?
佩尔松: 不算吧。我确实有存一些旧 PC 游戏的盒子,因为挺有意思的,但不会说我是收藏家。我不会去拍很多的照片,不会多愁善感,我更愿意活在当下。我从来不会去看(旧)照片,不过我会去看别人拍的一些食物照片,会觉得(食物)更加美味。
媒体:真的吗?
佩尔松: 是的,就像有个很好的侍酒师在给你描述酒,向你宣传,给你建立了预期一样,你会觉得酒更好喝。
媒体:你有养宠物吗?
佩尔松: 没有。我对猫和狗过敏,而且养宠物你得多到处走动。
媒体:还有哪些我没有提到的你想说的吗?任何想让全世界知道的事?
佩尔松: 我觉得我真没到能这种影响(全世界的)程度吧。人们能更加明白名人其实也是人这一点就好。他们(名人)并不是表面那样的,只是选择了想怎么展现。我认为跟一位你对他有成见的人、亦或是跟一个人的表象人格进行互动交流,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不是为了一些虚假的事物去攻击别人。比如说我有跨性别恐惧症,拜托,我从来没说过跟那相关的话好吧。你这是试图在网上发表什么声明罢。虽然我觉得这并不会有什么改变,但人们能够学会这些就好。
媒体:好的。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愿您愉快!
佩尔松: 非常谢谢你!非常有趣,真的。
全文完